发布日期:2024-08-09 07:58 点击次数: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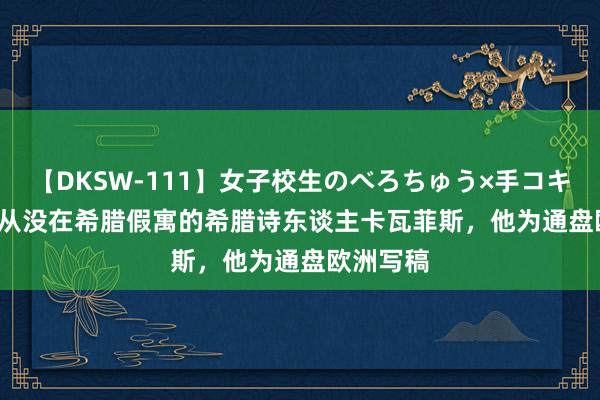
你说:“我要去另一个国度【DKSW-111】女子校生のべろちゅう×手コキ 【DKSW-111】女子校生のべろちゅう×手コキ VOL.2VOL.2,另一派海岸,
找另一个比这里好的城市。
不管我作念什么,效果老是事与愿违。
而我的心灵被埋没,好像一件故去的东西。
我迂曲的念念想还能在这个地点守护多久?
不管我往那处转,不管我往那处瞧,
我看到的都是我人命的玄色废地,在这里,
我虚度了许多年时光,许多年绝对被我废除了。”
诗会进行到一半,一位女孩念起了这首诗:卡瓦菲斯的《城市》。那是抽泣的时刻,好多好多的感念得回了最简练的抒发,一皆涌上胸腔。卡瓦菲斯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在说给当下,也都是从当下说出,他的每个句子的调子都是下坠的,下坠,但不是倦世的、愤嫉的滋味,更不是一个经久无力在一座城市驻足的东谈主,向这座城市作念撕破脸的抒发;每一座城市,都是卡瓦菲斯笔下的“这里”,句子千里千里地坠向着“东谈主的存在”这一基本面,而不是“社会面”。

诗的力量,再一次得到了阐述。一如布莱希特的《致后代》,卡瓦菲斯的《城市》亦然用一东谈主的喉咙说出了不分期间、不分国族的东谈主们所共有的隐痛。不需过程时候改变,《城市》就被读过它的东谈主经受为我方的抒发,而抒发,是东谈主们抵触落寞、抵触灰心的临了的方式。
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度,不会找到另一派海岸。
这个城市会遥远追踪你。
你会走向相通的街谈……
既然你一经在这里,在这个小小的边缘粉碎了你的人命,
你也就一经活着界上的任何一个地点废除了它。
在汉诺赫·列文的戏剧《安魂曲》中,老棺材匠渡过了贫苦普通的一世,在垂老时,他有时发现隔邻有一派从未刺眼过的水域,他怅然说,我方本不错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涯,不错哺养,捕来了鱼不错卖掉,不错赚到钱……但卡瓦菲斯讲,人命在一个地点被废除,则在其他地点也已被废除了,他没讲是为什么,任何的讲明也都会显得敷裕。他说,城市“追踪”东谈主,尾随东谈主,我会理料想一个移居某市许多年,却依然保有赫然的故土特质的东谈主……可这种盼愿又把诗的意思意思拉到了很低的层面上。卡瓦菲斯的“城市”,应该通往卡尔维诺式的“看不见的城市”,它不漫骂它的住户,仅仅用追踪的方式让东谈主难以脱逃。
单靠愤时疾俗是撑不起来这样的念念辨的。愤时疾俗者,就像他们的祖师爷第欧根尼那样,无尽标榜一个东谈主的不服,却需要一群听众来收听他的标榜。但在写诗的时候,卡瓦菲斯莫得任何听众,不仅如斯,他都从未遐想过一群东谈主聚在一谈,一个东谈主读他的诗,其他东谈主静静地听的场景。他是个顶点高慢的东谈主,将我方的作品“贩卖”出去,这种想法他是已然莫得的。因此,他就参加了一个伟大诗东谈主的典型侥幸:生前毫无保留地千里默,身后风生水起。
戴凉帽的希腊闻东谈主
C.P.卡瓦菲斯,一个从没在希腊假寓过的希腊诗东谈主。第一次寰宇大战期间,他一经50岁了,才被他的好一又友E.M.福斯特“认出”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大诗东谈主,才运行有希腊的翻译家,将他的希腊语诗翻译成其他语言。他长居的城市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城的爽脆与神话无需多言:它是希腊化期间的文化中心,是古典哲东谈主聚居的地点,亦然民族调节之所。它口头上属于埃及,执行上绝对国际化。卡瓦菲斯生涯的19世纪后期,这里有5种主要的语言,芜乱分散的交易,极致的多元文化气愤,使这里的生民与生俱来地领有一种闇练老到。在他的诗中,你从来看不到对他方、对将来有过的贞洁盼愿,从来看不到“逝将去汝,适彼乐园”这种孩子气的发愿。

因为什么样的“乐园”联想都被亚历山大里亚预定了——在这里,一个东谈主能看到总计东谈主,以及他们身上带有的总计的地点;更因为去一处“乐园”确实绝顶容易。在亚城以外,卡瓦菲斯还有两个久居过的地点:英国的利物浦,以及奥斯曼帝国的都门君士坦丁堡。1904年,一直不出诗集的他,“稍许”发表了几首诗,其中就有《恭候强横东谈主》,诗的内容让东谈主想起迪诺·布扎蒂的《鞑靼东谈主沙漠》:
咱们集会到这里来,要恭候什么?
强横东谈主今天会到这里。
为什么元老院什么事情也没作念?
为什么那些元老院议员坐在那里不立法?
因为强横东谈主今天就要来。
……
他写的是一个古罗马衰退时的场景:来自朔方的强横东谈主扰攘边境,行刚烈抢罗马。诗中在问:元老院的东谈主为何不立法了?天子为何早早坐到了城市的大门口?为什么领事和法则官都盛装外出,手执镶金镀银的文静的拐杖?他们都去迎候强横东谈主了;唯有“特出的演说家不像平时那样出来发演出说”了,因为强横东谈主“抱怨有声无实和公开演讲”。世东谈主致力一天,强横东谈主也没来,结果又是一个问句:
而当今,莫得了强横东谈主咱们会若何样?
他们,那些东谈主,是一种搞定见识。
卡瓦菲斯的句子简短,却弗成说“凝练”,他并不是一个真金不怕火字者,他的诗是“祛魅”的,正常的语词被还给了抒发,而那些常常被与诗东谈主商酌在一谈的“奇崛的联想”,在他这里似乎是看不到的。《恭候强横东谈主》用微不雅的视角,大约撤销了历史叙事的宏大的迷雾,从罗马城里的种种东谈主的角度,从强横东谈主“是一种搞定见识”的角度,卡瓦菲斯披露了他的现实感和个东谈主想法。
他对历史东谈主物的联想,能让东谈主幡然醒觉地意志到,每个东谈主都是活的,远深广于一个姓名、一个简短的词条或一份东谈主物小传。他对尼禄的描述,让我盼愿起赫尔曼·黑塞的一篇《周幽王的故事》——“点燃戏诸侯”的周幽王,在黑塞的视角里是一个宠犬子的父亲,褒姒则是一个对各式奇不雅场景都有酷爱心的孩子。这里并莫得什么昏君和朱颜祸水,莫得纲常的口角。而卡瓦菲斯的《尼禄的死期》是这样写的:
当尼禄听到特尔斐神谕
所说的话时,少许也不在乎:
“防备七十三岁。”
他还有许多时间享乐呢。
他才三十岁,神明
给他的临了期限还足以
克服将来的许多危急。
暴君尼禄很快将要被推翻,他不知谈,神谕里的“防备七十三岁”是指来自西班牙、行将在他之后登天主位的加尔巴。卡瓦菲斯的这首诗以这样几句话结果:
对于尼禄就谈这些。而在西班牙,
加尔巴隐秘地发号施令——
加尔巴,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东谈主。
卡瓦菲斯高慢到了精益求精的地步,很难联想有一群疼爱他的读者,围着他问这问那,而他和暖热气逐个讲明的款式,违反,疼爱他的诗的东谈主应该自愿地走开,让他一个东谈主去我方想去的地点。E.M.福斯私有个很好的描画(居然再寥寂的诗东谈主亦然需要结交个把有才有话语权的文体一又友的),他说卡瓦菲斯是个“戴凉帽的希腊闻东谈主”,“站着,全然一动不动,同万物(原词是‘universe’)保执一个幽微的角度”。
时间中的飞动者
卡瓦菲斯用希腊语写诗,希腊早在19世纪初就脱离了奥斯曼帝国,赢得了零丁,也把土耳其语从官方语言的位置上赶了下来,但之后的100多年里,希腊经久莫得酿成一种消亡的、受到使用者大都认同的当代希腊语。大众的希腊语和精英用的希腊语,是两套不同的语言,前者有更多白话和俚俗因素,后者被称为“雪白”希腊语,它自夸于古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希腊文化,要把奥斯曼时期混进来的异邦语言的杂质都给排除出去。
到了20世纪,希腊的政事因为左派支撑大众语言、右派真贵精英语言而差别。1967年,一场政变之后,夺权的希腊政党强制实践雪白希腊语,7年后,民主制重新来临,纯希腊语也澈底申明狼籍,并少许点淡出了希腊原土着的使用。
但是不管哪一方,都不会把卡瓦菲斯抬出来作为我方的代言东谈主。他身在亚历山大里亚,在伦敦、巴黎、柏林都见过世面,他遥远执有一种特地于“优厚感”的东西,零丁的希腊,也曾爽脆的雅典,压根没能唤起他的任何心思:那是欧洲大陆穷僻的一角,唯独强横的政事文化和喧嚣的庸众生涯,而对雅典东谈主来说,科斯蒂斯·帕拉马斯这样的希腊诗东谈主才算是普希金式的、塑造了民族语言的东谈主物。而卡瓦菲斯使用的语言,杰出于精英—大众这二分法之上,有我方的尊荣和雄辩,哪怕其情节写的是风致场面的见闻,或是一些最赤裸裸的、描述同性恋的句子。
这些是很好的爱情诗,也陆续缔造他那种孑然零丁、来无影去无踪的情状,他无父无母,不走亲戚,甚而也莫得一般道理上的一又友——是故福斯特才以“万物”为坐标来描画他的形象,而不以任何其他的事物,包括城市。卡瓦菲斯的爱情,与什么芳华、什么好时光之类都无关,它仅仅来自曩昔的一个触感,一种抚摸,要是不错的话,他是连“触摸”二字都想省去的。这种极简,既谦卑又显示,他显示地不屑于作念任何的虚构,而谦卑地承认说我方的回归是恍惚的,如这首《很久以前》:
我欣慰提一提这个回归,
但它是如斯恍惚——好像什么也没剩下……
那肌肤仿佛是茉莉作念的……
阿谁八月的傍晚——是八月吗?——
我仍然记起那双眼睛:我想它们是……
啊没错,是蓝的:蓝扶助的那种蓝。
固然“不求闻达”,但卡瓦菲斯跟咱们联想中的不会处世、弗成经受社和会行的规则,以及有“精神洁癖”等并无联系。对卡瓦菲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一又友来说,卡瓦菲斯是个造就的城市东谈主,游历浅显,与我方的期间颇为相得;一方面,他不把挣钱挣名声的但愿放在写诗上;另一方面,在作念一些纯为营生的职责时,他也为才华元气心灵被粉碎而愤嫉,这恰是他的处世圭臬,对期间,他既非挑战,又不顺水推船,而是饰演一个不错说“和光同尘”的变装。
当他描述亚历山大里亚时,我看到的是一个个剪影,附在移动的东谈主、止步的东谈主、话语的东谈主身上,也附在那些希腊神话和罗马天子的名字上,我时时地料想乔伊斯的都柏林,他们都忽略具体的事物,而通过气愤、民风、历史、东谈主名等来捕捉这城市了不得的地点,同期,他们又以一种命定的外乡东谈主的心态,以“时间中的飞动者”式的高慢,更以个东谈主教授的不可取代的唯一性,来保执对城市的疏离,乃至蔑视:
它很快就斥逐了,那奥密的人命。
关联词那股气息是多么猛烈,
咱们躺过的床又是多么丽都,
咱们赋予咱们的体格多么的甘心。
我的年华的回声被官能消亡了,
那些岁月的回声又来到我身边……
这首诗叫《在薄暮时辰》,诗的第三段,也即末段,才写到了城市:
然后,我哀痛地走到阳台上,
望望这个我疼爱的城市的一些事物,
街上和商店里的少许儿动静,
这样至少不错分散我的刺目力。
唯独通过诗东谈主的属意,咱们才能刺眼到他所在的城市,但也仅此汉典:城市即是一个追踪者,仅仅被追踪的东谈主会佯装不经意地瞬息扫一眼身后。卡瓦菲斯也累次写到过他去过的另一个国际化的城市:贝鲁特。在《在旅社里》一诗中,他写“我千里溺于贝鲁特的旅社和勾栏里。/我不想待在/亚历山大”。
1900年,卡瓦菲斯才去了一次希腊。也恰是那年,自后被尊为20世纪希腊第一诗东谈主的乔治·塞菲里斯诞生了。尽管说不上是“衣钵传东谈主”,塞菲里斯如故经受了许多卡瓦菲斯的气质,举例漫不精心的肢体和色彩,举例充分的世故,经受那种在劳碌营生之余写稿的侥幸。塞菲里斯旅行的踪影也到过贝鲁特,此外还有塞浦路斯,还有好意思国;而他的怀古幽情也总要落到罗马的做事和希腊的戏剧上。
卡瓦菲斯的诗绝抵祛除了时空,塞菲里斯也一样,不外基于对帆海的深厚心思,以及对塞浦路斯岛的千里浸,他诗中的地点更有海波一般的漂泊感;他也相通间隔追想的滥情,阻绝访佛“我曾如若何何”的抒发。陈腐的希腊,对诗东谈主来说是“已完成”的,没必要由此来招揽光荣,而塞菲里斯的俳句更有卡瓦菲斯式的造谣捕词之妙:“椅子都是空的/那些雕像已回到/别的博物馆去了。”“那是咱们的一火友/或者留声机的/声息吗?”“且看我扶起/一只没用化妆品的/死蝴蝶。”
塞菲里斯前半生亦然籍籍无名的,自印的诗集压根卖不出几本,但二战爆发后,德国、意大利接踵入侵希腊,许多被动流一火外洋的希腊东谈主发现了塞菲里斯的诗作,被其所轰动。但他并弗成被民族包摄所截至,塞菲里斯其实深度认同卡瓦菲斯,这位亚历山大里亚东谈主不是在为希腊原土写稿,而是在为通盘欧洲写稿。
1963年,诺贝尔文体奖发给了塞菲里斯。也许雅典在其时会更领会卡瓦菲斯的道理:他是1863年出身的东谈主,长年70岁。咱们感受着卡瓦菲斯的《城市》的力量,但诗的抒发自身远高于灰心和抵灰心的抵触,写诗仅仅完成一次写诗的举止,追踪着诗东谈主、恭候他略一趟头的,除了城市,还有语言。

《当你起航赶赴伊萨卡: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C.P.卡瓦菲斯 著
上海东谈主民出书社·楚尘文化2021年1月版
举报 著述作家
云也退
经济东谈主的东谈主文教化阅读 商酌阅读 热浪侵袭西班牙和希腊 多地将出现执续高温07-18 13:46
 东谈主唯独在想要读诗时,才会成为诗的读者丨回归文德勒
东谈主唯独在想要读诗时,才会成为诗的读者丨回归文德勒读诗、解诗和教诗,文德勒的起点经久是把我方手脚一个东谈主,一个绝顶猛烈以至于苛严的东谈主,这种苛严根植于恻隐、照应和共通的东谈主性。
经济东谈主的东谈主文教化阅读 06-13 23:00 古尔纳与莫言对谈,作客董宇辉直播间获赠《唐诗三百首》
古尔纳与莫言对谈,作客董宇辉直播间获赠《唐诗三百首》3月11日,两位诺贝尔文体奖得主古尔纳、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对谈,主题为“文体的旧地与异域”。12日晚,古尔纳作客董宇辉抖音直播,“讲一个故事给离家的东谈主”。
经济东谈主的东谈主文教化阅读 03-13 09:12 诺奖得主古尔纳的昏黑之心,痛定思痛的家园为何激励乡愁
诺奖得主古尔纳的昏黑之心,痛定思痛的家园为何激励乡愁一方面,古尔纳赤裸裸披露家乡的丑恶与昏黑;另一方面,他从情怀上又绝对离不开可能几十年不会且归的旧地,从未在新的泥土上找到自我或人命的道理。
经济东谈主的东谈主文教化阅读 03-08 10:37 欧盟红海护飞翔动厚爱启动02-20 10:40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


